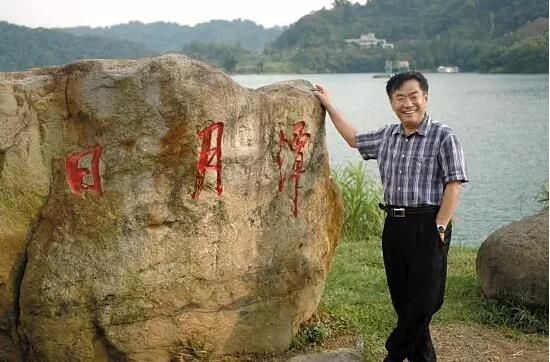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富仁,著名学者,1941年生,山东高唐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2002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倡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理念:“新国学”。
本文节选自王富仁《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
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清高,这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较容易做到的,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极难极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家里有几亩地的,读了书,当然愿意去官,但实在做不上,或者能做上但厌恶官场的那些繁文缛节,也就可以不去做。家里的地有长工们种着,只用少量时间过问一下,多数时间还是自己看看书,写写字,画画画,与同类的读书人聊聊天,因为平时就不太关心钱的事和官的事,所以自己的诗里、文里、字里、画里,就没有世间的这些烟火气,通体的“清”,通体的“雅”,连骨头里都透着一股清香味。但到了我们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这里就不行了。我们没有了“恒产”,也就没有了“恒心”。文化成了一种职业,我们得靠它赚钱吃饭。
虽然大家都感到文化需要独立,但从“五四”之后,独立的文化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时,文化是与其它社会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其它社会事业的肌体内发育滋长的。它像一个寄生虫,得寄生在人家的躯体上,才能吸食到一点营养,得以求生和繁衍后代。因为它是寄生在别人躯体之上、吸食别人的营养而生长的,所以因所寄生的躯体的不同,彼此之间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有了彼此不同的文体形式。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寄生在三个社会事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它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文体形式。这三个被寄生的社会事业一是教育,二是政治,三是经济。
我原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教书匠。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写书的,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学术专著”。但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就写不出学术专著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整块的思想已经写完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文化、学院派文化、社会文化一齐繁荣。中国的政治家要改革开放,要把自己新的政治方针宣传出去;文学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多经历、很多感触,是以前的文学艺术家所未曾表现过的,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表现出来;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话要说,从1949年以后没有说清的一些道理都想说个明白。国民有政治热情,学生有学习热情,读者和观众也有情感体验的热情。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非常的热闹。但没有多长时间,人们的热情就都转移到政治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政治是个最庞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体是不那么容易变化的,不像学院派文化,昨天还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找出了很多的证据、很多的理由,今天就又找出了很多它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证据和理由;它也不像文学艺术家一样,今天还是现实主义者,明天就成了现代主义者。政治结构太庞大,人太多,又得有统一的步调。要变就得一齐变。变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与此同时,政治文化还是一种权力文化,在中国的传统里,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都是在政治文化的统一指挥之下的。政治文化当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变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而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却像留不住把的自行车,老往前冲,就与政治文化发展的步调不一致了。这一下,就让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分子把热情转到政治改革上来了,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都带上了政治色彩,而政治文化是一种现实性、实践性、时间性很强的文化,对于政治文化,学术论著就显得有些钝了。弄上两三年,写成一本书,出版社还不知给出不给出,即使出了,时过境迁,与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对不起茬来了。所以那时起关键作用的是论文。论文来得快,又是严肃的,学院派文化和政治文化都有其严肃性,二者就有了共存的基础;那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更繁荣了,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文学创作本身,而是文学评论。比起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观点更鲜明,现实性更强,文艺观与政治观在文学评论中更易获得统一性。政治文化是宣传文化,它得快些,但又得严肃些,学院派的论文和社会文化中的文学批评更容易具有宣传性,更容易带上政治色彩。
我那时也是写论文的,并且声明不写短文。因为短文太尖锐,谈当下敏感的问题容易引起误会,对人不利,对己也不利。但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变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得靠政治结构内部的力量,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是帮不上多大忙的,弄来弄去,就把事情弄糟了,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迅速低落下来。在这个时期,学院派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专著又多了起来,但领导学术潮流的已不是论著,而是史著。论著重理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搞理论搞不出新名堂来了,而史著是重资料、重学问的,把前一阶段形成的新观点与更具体的史料一结合,就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出了新葩;社会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身,特别是长篇小说与电视连续剧。在这个时期,我没有跟上点。写学术专著自己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写文学作品不是自己的本行,也没有这方面的天才。那时的我很悲观,没有更多的话要与自己的同胞说了。90年代的中期之后,经济大潮掀起来了。社会文化是直接依赖经济的。经济的大潮在文化产业上的影响是报纸业的兴盛。80年代是学术刊物的时代,90年代是报纸的时代。连这时的刊物也报纸化了,登的是短小的文章,时事的报导。报纸的繁荣带给文体的影响是散文、随笔的繁荣。这时的学院派文化往外转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说完了,西方文化理论界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占了上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文化守成主义、新儒家学派,都是从异域移植到国内的。英语成了我们的第二国语,中青年一代都是精通英语的,西方的思想学说通过他们的努力占领了中国学术界。
我是在中国拜苏为师的历史时期学着俄语长大的,不在英美文化派这个流里,自己又早已离开了正统派,这时在学院派就站不住脚了。虽然自己曾声言不写短文,但这时来约稿的都是报纸编辑,写的短文也就多了起来。散文理论家说散文中有一类叫做“学术随笔”,我也姑称之为“学术随笔”吧!
我与“五四”
我是通过鲁迅了解“五四”,又从“五四”了解鲁迅的。
最早知道“五四”,是从小学和中学的课本里,那里面讲的是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学生运动。我对这个“五四”,不知为什么,印象并不深刻,好像对我并没有发生多么明显的影响。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胆小怕事,从小学到大学,凡是学生运动的事,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不大敢参加。我对“五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中学读了鲁迅的作品之后。那时才知道,除了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学生运动之外,还有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实际是在1919年以前的1917年就有了,它也不是在5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我对人们称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到有些奇怪,但恰恰是这个不能算作“五四”的“五四”,对我的影响既深且巨。当时读了鲁迅,很喜欢鲁迅,因而也就很喜欢“五四”。我想,“五四”给中国产生了一个鲁迅,而鲁迅又给我们写了这样的作品,足见“五四”是挺伟大的。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呢?上面说过,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农村,人是很少的,人与人的关系很单纯,那时大人教给我的是儒家的礼法。到了后来,读了《论语》和《孟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我没有读《论语》、《孟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懂得了其中的大部分的道理,那是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学到的,是大人们以身作则给我“则”出来的。但到了城市里,接触的人多了起来,知道的事多了起来,就有些应付不了啦。我那时又弱又小,打架打不过人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没有任何办法,总觉着这个世界有点妈妈的,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有点妈妈的,并不像大人们、老师们、领导们说得那么好。这时候,多么想把人想得清楚一些、把事理解得深刻一些啊!当时也读过一些其它的书,老师和领导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总觉着有些“隔”,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及至读到鲁迅的杂文,心里才觉得亮堂了许多。从那时,我才知道应当怎样观察人,怎样理解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在过去,社会、生活、人乃至自己这些自己很难驾驭的东西,对自己是一种沉重的压力。读了鲁迅之后,我才感到,世界虽然荒谬,但却不是没有趣味的;自我虽然渺小,但却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就给了我一种做人的感觉,做人的勇气。我这一生,经历过很多不如意的事,但却没有被这些事情完全压垮。越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个世界在你面前表演得越充分,你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就越多,你也越是能够看清自己要走的路,做人的勇气也就大一些。我认为,这就是鲁迅杂文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得感谢鲁迅。是他,教会了我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现代世界上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做人。
当时读鲁迅,没有想当作家、当教授的意思。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考了一个研究生,研究起鲁迅和现代文学来。在这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了解得才多了起来。陈独秀了,胡适了,周作人了,李大钊了,《新青年》了,《新潮》了,白话诗了,现代小说了,传统文化了,外国文化了,人道主义了,个性解放了,等等,但对这一切,我仍然是依照鲁迅的理解来理解的。它的自由的要求,民主的要求,科学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要求,文化革命的要求,文学革命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异常自然的。孔子那个时候,只要维护好皇帝的政权就行了,只要当官的不贪赃枉法就行了。当官的能把官位坐稳,老百姓也有个安生日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不行。现代的社会得靠全社会的人的共同努力,人民没自由怎么行?政治不民主怎么行?不讲科学怎么行?对整个世界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怎么行?世界变化了,人的观念也得变化;人的观念变化了,文化、文学不变也得变。文化革命、文学革命又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那些已经有了特权的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可怕的?直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厌恶“五四”,厌恶鲁迅。我认为,他们想的都不是我们中国人怎样在现代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发展起来,而是别的一些事情。当然,“五四”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给我们做好了,鲁迅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告诉给了我们。要是那时的人把任何的事情都给我们做好了,我们再做什么呢?他们提出了自由、民主、科学这些现代的中国人需要追求的东西,只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具有的,“五四”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韩愈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朱熹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这一切是“五四”告诉给我们的。我认为,这就足够了。至于怎样实现它们,什么时候实现它们,在实现它们的道路上还会有哪些困难,会不会走弯路,会不会有牺牲,这都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应当思考的。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