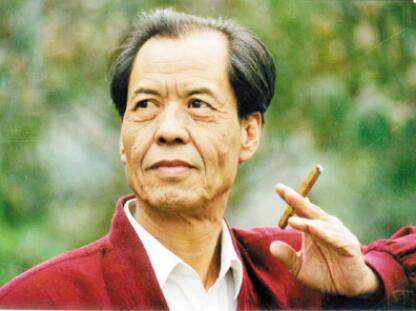
之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 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 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 8 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 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 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 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 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 我的笔刚刚触及到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 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 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粟, 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 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 和我记忆里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 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 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 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 1985 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 正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 短篇小说也还在写, 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 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 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 不着重故事情节, 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 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 而努力寻找我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 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 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 我在 1985年夏天以前, 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 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 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 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 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 也正写到顺手时, 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 10 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 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 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 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 而是截止到 1985年夏天, 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1978 年文艺复兴以来) 。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 开会研究讨论, 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 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 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 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 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 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 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 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 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 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上, 一望无际的草原, 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捲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 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 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说时, 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 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青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 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 邪念刚萌而未生, 就被父亲察觉了, 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 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 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 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 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我最初的影像, 就是原上一幢镂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 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 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 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的长篇的写作, 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 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 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作短暂修整时, 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事迹报道, 竟十分激动, 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 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 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 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 不是经管的失措, 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 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候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 5 千字的报告文学, 随之又写了 8 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 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 1986 年的 8 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 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 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 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 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 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 淌过家门前的灞河, 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 再穿过对岸的村庄, 到公路上搭乘通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 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 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 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座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 所幸有一个右手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 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淡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 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 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 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 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 而且行走其中, 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 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 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 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 且不说太远, 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 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 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 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 8 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 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馆,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历史资料保存在什么部门, 以及借阅需得经过什么手续……
之二: 卡朋铁尔的到来, 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查阅资料的举动, 大约有两个因素, 一是如前所述, 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 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 我很清醒, 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 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 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 17 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 我既缺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 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 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 1950 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 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份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 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 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作民办教师, 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 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 是一幢拆除了不知那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 嘻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 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 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 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 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 整整十年。十年里, 我把公社大小 30 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 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 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 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 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 不仅在于生长于兹, 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 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 整整在其中干了 10 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 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 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 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14年, 成为至今依然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 起码不落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 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社会的浮泛和肤浅, 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 年以前的乡村, 我得进入1949 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 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 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 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 却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科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 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 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许多年青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 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 学习现代派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 几年之后, 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 却几乎无声无响, 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 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诀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 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 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 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 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 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 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 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 惊讶到瞠目结舌, 竞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 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王国》框不进去, 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它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王国》在拉美地区文坛引发的震撼自不待言, 被公认为是该地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 一批和卡朋铁尔一样徜徉在欧洲现代派光环下的拉美作家, 纷纷把眼睛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许多年后, 拉美成长起一批影响欧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体, 世界文坛也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概括他们艺术共性的名词———魔幻现实主义, 取代了神奇现实主义……我在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 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 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 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 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 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 即白鹿原) 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 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 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 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 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 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 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 尤其是我的父亲, 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 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 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 我年青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逝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 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叶子的村庄, 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 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 因由只出于一点, 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 曾是我的家乡隶属的县, 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 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幅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 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 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 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 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分类着历史沿革, 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 咸宁和长安多所变更名称, 唯独蓝田自秦设县以后一直延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峪谷地, 不仅有文字叙述, 而且有图示; 历代的县官名称简历和重要政绩, 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 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 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 先后都考中状元, 都有文集著作, 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 被杨献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出来, 遭到毛泽东点名批评, 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 在一所二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上级指示, 全乡( 公社) 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 一种愧疚使我无言, 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作过“表态”发言, 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 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 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落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 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 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 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 尤其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时, 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 竟然有四、五个卷本, 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 不仅令我惊讶, 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 看到记述着××村××氏, 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 不幸丧夫, 抚养孩子成人, 侍奉公婆, 守节守志, 直到终了, 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 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 事迹大同小异, 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 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 只记着××村××氏, 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 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 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 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 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 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躁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 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 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 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 或者说挽歌, 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 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 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 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 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 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理。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泼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 虽然上不了县志, 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 竞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 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 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 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 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 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正。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功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 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 需要某种沉浸, 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 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 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 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 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 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 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 许是耽于种种顾虑, 谈得很浅, 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 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 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 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 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在他手上, 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 积累囤攒了几年, 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 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 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 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 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八家院, 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 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 没有再添一间新房, 也就无人迁出老宅, 直到 1949 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 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 个子很高, 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 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 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 是一种无以为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 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 这个人的秉赋、气性, 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 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熔进这个人的血液, 不再是干死的条文, 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 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 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 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 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 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 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 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环境里, 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 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 遂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 竟有两年多时间, 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 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 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关注, 要尽可能准确地把准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 以及他们的心理机构形态; 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 更具妙趣的是, 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 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 当是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 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 不是史学家的考证, 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绎和阐释, 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溶注到多色人物中, 几乎在此前( 小说写成前) 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 年初, 在中断了半年写作, 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 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 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坦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 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颠, 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 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 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 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 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 却无一不是期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 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 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 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 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 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 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 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 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 何况禁锢了的心灵, 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坦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 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 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 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