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徐德金,中新社记者。早期诗歌受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影响,形成意象唯美、形式奔放的风格。近年重执诗笔,追求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诗歌更具内敛厚实。
◇◆◇
彼 岸
彼岸在高原
在绿谷、山崖、溪壑的任何角落
彼岸在漫天的锦绣铺向四周
在微凉的深秋
似曾相识的众生,未曾谋面的异乡
该开放的花都竞相绽放
该守候的时光
却没有等到四季轮回
彼岸,浓缩成今夜一丝小雨
以及车外难以辨识的面孔
在对视的瞬间
开始怀疑一本书的故事
怀疑这样一个平行的时空
阴差阳错的真实存在
渡己,却无法渡人
去到彼岸
一次秩序的生长
未必在繁华落尽之后
真相只有一个——
心灵抵达不到
彼岸,在此岸
也一定不会
2017年10月11日晨于墨西哥城

▍诗评
赵小波(诗人):
“时间”是徐德金近期诗歌一个重要的概念,他以只可感觉而不可直观的时间作为基调,伸展语言的空间张力,让艺术翅膀在想象中翱翔,俯视感知的客观对象:“彼岸在高原/在绿谷、山崖、溪壑的任何角落/彼岸在漫天的锦绣铺向四周/在微凉的深秋”。
◇◆◇
老 墨
你无法长出一对犄角
去阻挡一只大象
那时候雨下了
一个星期,而你的位置
决定你的方向
你就像遥远的远方
失散一万年的兄弟
你就是一个久违的邻居
在陌生国度里徘徊
(我们曾经遇见在北美
Lee Highway红绿灯交换之际)
高墙装饰了北方誓言
在南方,心头垒起一块块砖头
你如何去拯救一个新大陆
那仿佛变成旧世界的一部分
新旧之间
荒漠长出荆棘
刀割一般的伤口
再痛,也要把血流向内心
那是你的国度
如鹰如啄,如诉如泣
2017年10月19日
◇◆◇
慢 板
新大陆断成一管长箫,水声幽咽
从南方到北方,沿着山丘平原的连绵
新大陆瘦成一支弯曲的芦苇,束腰到不能呼吸
海水漫到眼前浪花点缀胸襟
伊比利亚有多远
记忆就有多远
当郑和的船队逶迤于海上
美洲,还是一块沉寂的大陆
迟到者是一名大海的儿子
航行的线路曲折而孤寂
他是骑着一匹骏马的渔夫
从辽阔的大西洋
飞驰过,无数风浪
每一声汽笛都那么苍凉
每一次飞翔都那么舒展
当海水涌进那管排箫
太平洋与大西洋像山谷间
深情的对歌,即便隔着远山远水
即便盛满地球所有的眼泪
2017年8月29日
▍诗评
朱必圣(诗人,评论家):
这是诗人徐德金描述记忆的表达方式,甚至不仅只是描述记忆,而是描述创造的记忆。请记得“伊比利亚有多远记忆就有多远”,这是只有用心灵才能感受的景致和情感。它不需要更多的词汇去演绎、解释。它直接呈现在你面前,它跟存在一样真实而不可撼动,它既是遥远的伊比利亚,又是深远的历史和个人记忆,是你不可漠视的。
◇◆◇
序 曲
切,那个该死的格瓦拉
像飞行器在丛林盘旋,像飞鸟
海边褐色木屋的阁楼上
他如此苍茫,瞭望一条鱼
在礁石的缝间暗潮汹涌
站在窗前,海明威
像加勒比海
一片孤帆
雪茄燃起的白烟
如一支长矛投掷天空
风徘徊于衰败的街道
哈瓦那革命广场尾气相随
每一扇小小的窗口
都试图打开,更高处比如古堡
就能看到海的天际线
和比天际线更加辽阔的岁月
卡斯特罗像神话一般
把自己埋葬了
连同他亲手点燃的篝火
而所有人民的细软
被拉链紧紧锁住
只剩格瓦拉的帆布包
那个匆匆的战士
风靡世界
“切,我的儿子”
2017年8月26日
▍诗评
毛翰(华侨大学教授、评论家):
滤除了所有的W的诗,有时还是不免显得过于高蹈,与世隔膜了,这时候,诗人就忍不住要走到台前,抵近现场,指点历史和时代了。
这首诗不知为什么叫《序曲》?是感慨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的革命理想、革命初衷吗?哈瓦那革命的序曲多么美好,多么勾人遐思、让人向往甚至追随。可是它的接下来的各个乐章呢?“雪茄燃起的白烟/如一支长矛投掷天空”,曾经的革命理想,这样浪漫又虚幻。
“卡斯特罗像神话一般/把自己埋葬了/连同他亲手点燃的篝火”,这是卡斯特罗一代决不相信也决不承认的残酷的现实。切·格瓦拉的早逝恰恰是他的幸运,“那个匆匆的战士/风靡世界”,成为永远的偶像和图腾,而卡斯特罗的高寿却是他的悲哀和宿命,他的遗产是“风徘徊于衰败的街道/哈瓦那革命广场尾气相随”。
在西半球,在曾经的革命圣地古巴,诗人有太多的感慨难以尽情抒写,其点到即止的语象,对于心有灵犀的读者,也足够了。
不忘初衷,如今已是流行语。可是,哈瓦那的革命初衷该如何记取,序曲之后,其主题如何呈示,如何发展,如何变奏?这课题过于沉重,已非一首自由诗所能承载。
徐德金写诗沉寂许多年,更不是今日诗坛的活跃分子,在形形色色的诗人聚会上,几不见他的身影。他只是在默默地写诗,灵感来袭时随性地写着,他的诗不大发表在主流诗刊,不大见于诗歌选本,也不大为评论家关注。只在微信朋友圈,不时地见到他的新作。他像是诗国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惟其如此,与诗国的圈群和套路全无干系的他的诗,才更显几分古拙朴素。
我不大喜欢所谓专业诗人,不大喜欢那些天天写诗,除了那种分行文字,别的啥都不会的人。徐德金早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就曾是采贝诗社社长。此后多年,他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国内国外跑新闻。他不写游记散文,炫耀其见多识广,却惯于夜深人静之时,回到自我,回到诗。其诗不关乎名,不关乎利,故而纯净本真。
朱必圣(诗人、评论家):
只有诗歌才能展开如此魅力四射的表达,“他如此苍茫,瞭望一条鱼”,“站在窗前,海明威像加勒比海一片孤帆”,如此诗句,你不能用新闻式的视角去寻找它的真实形象,你也不能用普通的社会和生活经验的认识去认知它的意义。你只能紧随其后,尽可能让心灵抵得住诗歌语言的冲击,感受其中对于世界与生命的超越性感知,感受其独特性的表达方式闪现的意义光芒。
◇◆◇
影 子
我从众生中找到藏匿的影子
它被日光钉在墙上
月光放它到水里
灯光下它仆倒床上
目光是它最丑陋的发现
影子是我丢失的附件
怕光也怕夜
影子是我身上脱下的外衣
比我浪漫,但比我孤单
影子时常找不到回家的路
有时候它忘了自己
藏匿的方向
我不轻易
去踩影子的哪个部位
我盯着影子,思考它喋血的现场
2017年9月25日

▍诗评
毛翰(华侨大学教授、评论家):
影子是什么?是走过人世的我们,试图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试图贴近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试图影响世界的一种方式?影子投射在世上,与我们的人生若即若离,影子是我们人生的或被拉长或被放大或被压缩的一种存在。走过时空的人,与人的影子,谁更真实?走过光明,人与自己的影子都有强烈的存在感,走过黑暗,人与自己的影子则相互疑虑。人生百年,人与自己的影子同在。百年之后,只有影子还在怀念我们,阐释我们,见证我们的曾经。
诗人徐德金笔下的《影子》,给我们以启迪,以感悟,以警醒。上述种种,可能就是《影子》勾起的我们的诸多思绪。但这思绪再多也只是思绪,不是诗。诗是什么?诗是“影子是我身上脱下的外衣/比我浪漫,但比我孤单”,诗是“我不轻易/去踩影子的哪个部位/我盯着影子,思考它喋血的现场”。诗是诗思承载于“影子”这一意象之上,是“影子”这一意象承载的许多欲言又止、无须明言的哲人情思。诗人与读者心有灵犀,只把一只造型别致的夜光杯打造出来,呈献给读者,至于杯中所斟,是葡萄美酒,还是别的什么佳酿,则需要读者自己去品味,去斟酌。
影子“比我浪漫”,也许还比我时尚,比我光鲜,比我神气。世人看到的,只是我的影子,世人看不到我,看不到那个被影子的外衣包裹的我。同时,影子也“比我孤单”,影子超然于尘世的熙攘,自外于人生的繁华,它冷静、孤寂、随缘。“影子时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时候它忘了自己/藏匿的方向”,诗以最简练的语象,表达着诗思的深邃和淡远。
赵小波(诗人):
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与探求,几乎贯穿徐德金的近期诗歌,其中《影子》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影子是光照射在人的身体的外化影像,是主体的虚幻映像与延伸。影子与主体相随,又独立于主体存在。诗中似“我”非“我”的影子,是人类的精神的化身:“影子是我丢失的附件/怕光也怕夜/影子是我身上脱下的外衣/比我浪漫,但比我孤单”;“影子时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时候它忘了自己/藏匿的方向”。这这里,精神是浪漫的,但也是孤单,回不去的家园,是失落、疑惑,甚至是困境,倾诉了诗人的无奈及悲怆。
◇◆◇
我屈服于时光
——给BC
我屈服于时光
时光是长满牙齿的风口
月色被星星吞没
花瓣渐次飘落
在你虚掩的日历
一些果实开始成熟
我将作恒久的守候
像守候一场西风
叶子离开枝头
快把岁月抓牢
你深深浅浅的夜
已从梦中逃走
2017年9月23日深夜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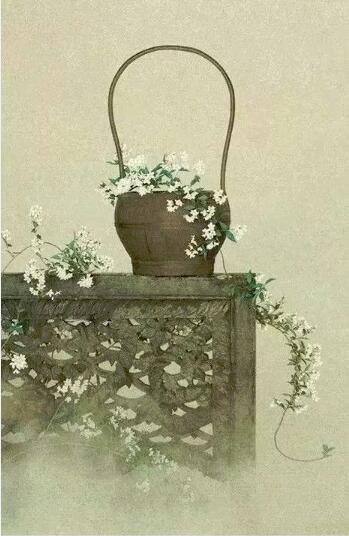
◇◆◇
苍 茫
大山横亘于前
像大海深处
桅樯如云
那轻舟荡漾
从荔园滑过
少年是一片浅笑
藏不下万水千山
大山打上补丁
北风撕开它的一角
江水缓缓流淌
如苍鹰在山顶盘旋......
大海重归于寂
大山一般沉默
2017年8月5日

◇◆◇
路过朱紫坊
朱门把雁门轻轻带上
月光独照青石板
水的姿势亭亭
古巷里流出了细语
今晚一片轻舟
穿行于城邦之上
高擎时间之烛
眼泪流淌不尽 也无法
照亮夜行时的清癯
直到日出东方
曲巷所有的声响
背光的所有幽暗
如是一个路人
不经意
就像马头墙摇曳的风铃
而酒依然温热
即便如此
如此只是偶然
就像那年的萨镇冰
路过朱紫坊
2017年7月19日
▍诗评
赵小波(诗人):
在“高擎时间之烛/眼泪流淌不尽 也无法/照亮夜行时的清癯/直到日出东方”街区,诗人聆听“曲巷所有的声响”,管窥“背光的所有幽暗”, 寻觅“古巷里流出了细语/今晚一片轻舟/穿行于城邦之上”,追溯昔日繁华中的宁静,宁静中的盛世,感受“就像马头墙摇曳的风铃/而酒依然温热”的历史。时间逝水流年,世事交替不归,这不仅仅是诗人对历史的感叹,也是社会进程的真实体现。
◇◆◇
速度十三行
脚步移动的速度比河流还快
它可以折算成时光
从甲地到乙地的形色匆匆
你无法阻止一场哗变
它们从树上逃脱
满地金黄,柔软得无法扶起、站立
但指控被春风裹挟
转眼夏日缤纷
地表已没有生存的理由
生存意味着残喘
在浓荫覆盖的面积
那些车轮滚滚
比仓促更加高级
2017年7月19日
▍诗评
赵小波(诗人):
诗人巧妙地通过意象的媒介,让抽象的时间可以直观感知,甚至触摸——“脚步移动的速度比河流还快/它可以折算成时光”。
◇◆◇
西门外
1
飞过油菜花地的纸鸢
临近城门
驮着干稻草的板车
也临近城门
城里有不同的声音牵引
我的目光
从不一样的季节
凝视大街小巷
每一件新衣
2
阳光认识每一粒稻谷
就像我认得它们
金黄的外衣
嗮谷场离秋天很近
我试着做了个春天的梦
3
空气凝固的时候
汗水流过腮边
时间在荔枝树上
刻下一道伤痕
知了从正午向晚间
由青变红
4
风翻开阁楼上每一页纸张
从此不再离开
从此眼里长出忧伤
就从一块薄冰开始
麦苗不能屈从于风的安排
还有紫云英迎风凛冽
热烈就像旌旗十万
5
等待需要耐心
它甚至比一个上午要长
因为远方太远
38路公交车也不能到达
归来变得遥遥无期
当我们试着回忆
这一段抚不平的路途
却不会变短
2017年5月29日

▍诗评
赵小波(诗人):
“阳光认识每一粒稻谷/就像我认得它们/金黄的外衣/嗮谷场离秋天很近/我试着做了个春天的梦。这样的诗行,需要高度的视野,开阔的眼界方能写就。
◇◆◇
台北车站
把时间投掷到随便一节车厢
南迴或是北迴,而交接就在此时
被城市捷运、计程车,被似曾相识的手
交接也可以无需空间、缺乏仪式
被城里的月光,被淡水河边的某一片晚霞
有时候虚无的声音遗忘在了车站
像车站周遭每一次自言自语,每一种各说各话
春风伏在了你的肩膀,再滑向你的锁骨
你胸前一片稻浪从花东纵谷吹来
那不是太平洋的风,不是
兰屿外海热浪的赠予
你从青花釉里脱颖而出的款款只能是
从唐山摇过浅浅海峡的橹桨
呀呀的余韵缭绕,车站变成码头
张开双臂,拉长海岸让送行者欲拒还迎
每一枚弹射出去的蓓蕾
从站台弯曲的回廊上纷纷飘落
远方更加遥远。出走
是最轻率的旅行
像兴高采烈的蚁群
下一站板桥
有如抚摸一截春风
匆匆的来,姗姗的回——或是不回
谁把台北车站看做终点
谁又把南京东路当成了故乡
2017年5月
◇◆◇
台中大甲
在大甲,我住汽车旅馆一晚
离镇澜宫三条街,我走了两个来回
颜清标从国外赶回大甲,致辞说
天下妈祖是一家,听者来自福建
我在旅馆打电讯稿,还能听到锣鼓喧天
门没有关紧,窗户也还开着
想听几声“烧肉粽”的叫卖,拖长音并且
婉转几条老街,就像那时的东边社
需要电源插座,标准与我相同
再来一盘蚵仔煎,味道跟马巷的一样
2017年5月
▍诗评
赵小波(诗人):
诗人将场景放置在离镇澜宫三条街的汽车旅馆,在一个似曾相识,又显陌生的空间,诗人觉得似乎时间有点尴尬,他在住宿的汽车旅馆与“离镇澜宫三条街”的街区“走了两个来回”, 希望“需要电源插座,标准与我相同”, 还“想听几声‘烧肉粽’的叫卖,拖长音并且/婉转几条老街,就像那时的东边社”(笔者注:东边社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里校中村,寒冷的冬夜,村民会为学生供应宵夜)。 虽然“门没有关紧,窗户也还开着”,但由对空间及时间窘境的叙述,表达了个体的境遇,感慨海峡两岸长期分隔所造成的,不仅仅是社会制度不同,也包括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
后 山
高山隆起,横断中央
鸟的翅膀刚刚触抵半山的枝桠
密林深处有逶迤的人群、马队
几棵香樟树倒向悬崖
石头滚落山涧
他们来自平埔,可能吧
另一种说法是从昙石山来
沿闽江漂流,向南岛
向着太平洋的浅蓝处、深蓝处
其实他们到不了那么远
大部分的人就近上岸、溯流而上
他们来到后山,打个盹
野猪、豪猪、黑猪从眼皮底下跑过
长矛追着它们,后来是火铳,现在换成麦克风
他们投票,锯山樟树做票箱
树叶上写下故乡的名字
站在后山他们大声喊,喊山喊海
山洪切开大山的记忆
他们将巨石推进大海深处
没有响声,涟漪也不曾荡漾
2017年5月
◇◆◇
以夜之名
以夜之名,万物收入囊中
吞噬各种声音,一句独白
在十字路口忧郁徘徊
连开放的花朵都保持缄默
鸟儿也不再唱歌
它们属于太阳底下的音符,所有的欢乐
大脑长出南瓜般思想,藤蔓爬过众墙
挡住外界的嘈杂,一切众说纷纭
孤寂是夜晚的凯歌
黎明前的呻吟,挑逗夜的神经
它是白天的另一副嘴脸
只为自己代言
是呵,黑夜看不到白天的白
白天也看不到黑夜的黑
阴阳对决,蹲伏一只怪兽
2017年4月21日
◇◆◇
蓝尾星
从天上跌落凡间
碎成更多往事,撒向草丛
小明提着灯笼,沿河渠
走向更深的深夜
这时候母亲在哪里唤我
在更寂寥的怀中,星星点点
瘦成几行字,在书本边缘
小明就是从书本爬出来的蓝尾星
一枚一枚摇动着蓝色的裙摆
又以蒲公英的姿势飞曳
断成了上半阙
我做了很多努力,有时候
闭上眼睛想象蓝尾星的前生
是否就是小明,小明是否刚刚合上眼睛
也合上刚刚打开的书本
瘦瘦的几行
亮亮的几行
竟变成一片空白
九十度角形成的天窗
2017年4月15日
◇◆◇
黑
湿漉漉的手,伸进
周六晚上,各式各样的眼神奔跑
闪电一般,跑过看台
就像白雾骑上灰墙
黑暗是假装的,墨镜之外
——“你看得见我吗?那边的”
只有荧光棒晃动
潜伏在歌声里
从古老岁月,穿过你的黑
我掀开苍穹的窗帷,看到繁星
2017年4月8日

◇◆◇
在那边
在那边,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游戏
哪个动作,什么表情
才能辨识身份,来的路上
是否同舟,还是相伴
我们要把深深的记忆埋在
往昔的时光。往昔,我们何曾珍惜
读书歌唱,早晚问安
在那边,我们已不能用语言唤起记忆
我们平行于相互的移动
走来走去,点头致意
最多握手作揖
那边连文字都是多余
我们都在一起
房间容不下那么多复杂的长相
不能用时间计算苍老
只能用气息
证明彼此的存在
我们将过着纸片一样的生活
不是随风飘舞,而是从此不再燃烧
在那边,水的温度和火的温度
都在一个标准
我们是否需要用更多的动作表情
重启某种程序
让精神复活
而不是聚在一起
做简单的游戏,把砖头搬开
在那边,没有爱情的话题
也没有下岗的叹息
每天围在一起
洗衣喝茶,挑水做饭
我们的手上都系着一条红线
那是尘世唯一的联系
从此不再走失
2017年2月25日

◇◆◇
扒开时间的裂缝
垂放到最低处,我的手
扒开时间的裂缝——
你所能见到的已不是我的容颜
我藏在悲伤背后不经意的回眸
成为生命的缺口都将全部流走
2017年2月18日
◇◆◇
穿过所有的手
我的手无力揽镜
无力抓一把
空气放在枕边
我的手穿过黑暗年代
穿过一头秀发
那已经不是
我的手
那爬满青藤的墙
在等一次岁月的流逝
茫茫九派穿过
从我的肩膀我的臂弯
我以鱼的姿势呼喊
从我的心肺
手无力,也记不起那年
上元节的温度
南后街以南
我看到举着的花灯
那手在风中舞动
在青石板上撒下一串笑声
我的手穿过所有的手了
有时我从他们的胯下穿过
我摸索着我的手
穿过窗外
走廊尽头
有无数的手臂呵
有掌声如盥洗室的水哗哗作响
而我却连一滴眼泪
都不能流淌
我的手,我的手
终于推开另一扇大门
白光覆盖了我的全身
我的身上长出一对奇异的翅膀
2017年2月18日
◇◆◇
别 梦
我装不了世界那么多纷扰
它们像倒伏在农田的水稻
等待一场台风收割
山洪、泥石流、滑坡后所有巨石的全部
以及穿针的线线穿过烽火连天
它们以蚕的姿势胡乱掘开春水
像一场欢腾的晚宴
出没于群山环抱
呕吐、歌唱;互相交叉、横七竖八
帆迎向浪浪涌向幸福的船舱
然后春梦覆盖它们
呻吟逐渐褪下
遗失了的时间
无法计算春宵一刻
有多重 在我别梦的一角
下一次,您突然到来的时间
是子夜抑或凌晨,都请提前说一声
我把所能做的梦把梦的所有时间都留给您
2017年2月6日
◇◆◇
无名渡
一定有个朴实的名字,只是早已忘记
送你到无名渡口,我们就此别过
那天的船像从弹弓飞出,我在岸上徘徊若无
一支江水从上游来,来自你笛声残处
你在江南,比江北萧瑟,我在江北牧鹅
就此别过了,我们就从无名渡别过
我忘记你是谁,什么归宿,什么来路
2017年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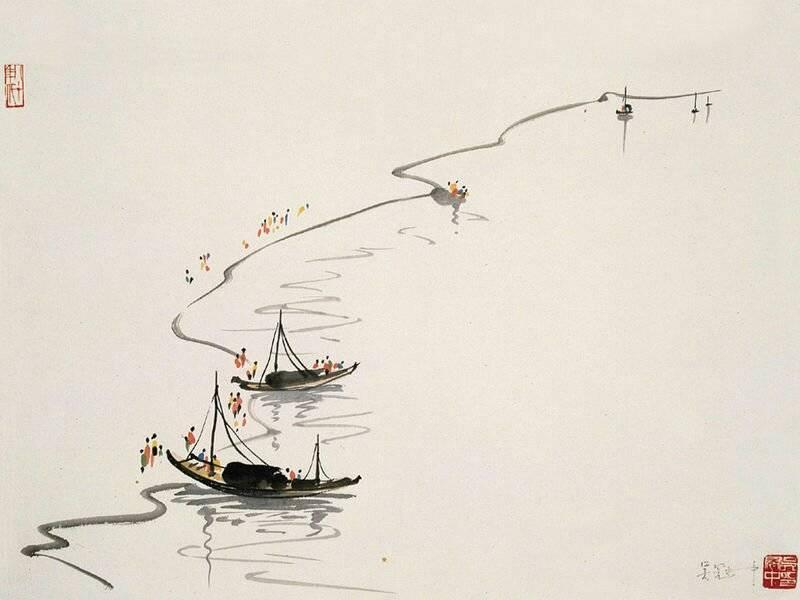
▍诗评
毛翰(华侨大学教授、评论家):
一个没有名字的渡口,一道没有名字的江水,一次忘了缘由的送别,甚至忘记了你是谁,什么归宿,什么来路?以及我是谁,什么归宿,什么来路?人生本是孤独的,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一个朋友偶尔相逢,随即离别,各自南北东西。朋友是谁并不重要,朋友的名讳事迹,也不必刻意记取。就像一个渡口,一道江水,那命名只是偶然的,本来就没有更多的意义。
新闻稿的要素是五个W, 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why(何因),一个H,how(如何。其实还是W,还是何,只是后置了)。到了诗人笔下,这几大要素全都消失了,失效了,只剩下不知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以及如何的一段人生感悟、感慨和感伤。我不知道,作为职业记者,作为资深诗人,作者是如何转换角色的。角色的频频转换,会不会像是倒时差,有所不适?也许恰恰相反,只有如此彻底的文体转换,如此富于挑战性的角色转换,才完成了一种过瘾尽兴的人生体验?
也许,滤除了五六个W的诗,才是纯粹的诗,纯粹的抒情诗、哲理诗。也有不曾滤除W的诗,那是叙事诗。诗人徐德金不大写叙事诗,因为那接近新闻稿。而新闻稿是职业写作,是稻粱谋,诗则是心灵写作,心灵的独白或呓语。写新闻稿的徐德金,是历史的记录者;写诗的徐德金,是人生的感悟者。
在此诗中,残存的具象的叙事因素,如“一支江水从上游来,来自你笛声残处”,“你在江南,比江北萧瑟”,“我在江北牧鹅”,也都经过了抽象、变形和诗化处理。
当然,司马迁的《史记》与屈原的《离骚》也有相通之处,《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诗人徐德金笔下无数的新闻稿,想必也可以做另外的解读,那客观的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诗的美刺和悲悯。
朱必圣(诗人、评论家):
“一支江水从上游来,来自你笛声残处|你在江南,比江北萧瑟,我在江北牧鹅”从徐德金兄今年所写的二十余首诗作中,拿出这首《无名渡》诗中的两句,即可感受到那种平静的力量,感受到无波、无流水起伏的汹涌。其实这就是发自诗人内在的秉赋。秉赋是种天成,它养育诗人的感受力和个性的诗歌语言以及表达方式。一支来自上游的江水与一支来自笛声残处的江水,汇流到一起了吗?其实对于诗人的表达而言,根本不需要什么江水,也不需要什么真正的笛声。它需要江水和笛声这样的外貌可以完美地传达出诗人秉赋中的语言品格,也就是能够实现一次对于存在的完美表达。对于一首诗来说,全世界只有这种表达,只有它是最完美无缺的,没有第二个,它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表达的意义。“你在江南,比江北萧瑟,我在江北牧鹅”,像这样的诗句,需要有人去演绎它吗?需要有人去问江北如何萧瑟吗?诗人说:“我在江北牧鹅。”这就等于创造。对于诗人而言,表达就是在创造存在,诗人以创造存在,来完善人类与世界。由此而言,表达才如此至高无上。
◇◆◇
时间的刻度
你踩着不变的步伐
我是仓惶中的小鸟
你不能用我的白发证明你的存在
你怎么证明自己属于过去、现在或者未来
岁月有痕刻在每一个角落
有思考的态度有纵情的模样
你把虚无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世界
你说你已经漫长几千年
我如何肯定你翻过的每一个瞬间
你怎么走过我的身旁,就像猫
怎么依偎你的身旁
我用一个迟缓的动作丈量你的刻度
用一次短暂的夜晚、一句话、一个辗转反侧
2017年1月6日

▍年度诗评
王柏霜(诗人):
德金兄2017年创作的诗,明显的具有一种自我精神力量的延续。他的一部分诗作从理性的、冷静的、甚至是旁观者的角度,从精神的厚度到感性的宽度,从容不迫地追寻着真相——时间、空间、历史、当代等等文化现象,甚至虚幻的影子也有类似于黑暗功效的隐藏起来的真实的“喋血”的现场。这些《苍茫》的“黑色之夜”,作为一个个高明的隐喻,追索着永恒的命题:命运的不确定性,时间的线条式单向性、历史参照系的固化性……它们体现了诗人对于这些不可控因素的焦虑,映衬出个体的虚弱与无奈。多样化、情绪性,空间位移感让诗人敏感的神经,在面对庸常事物与世俗生活时,体验着抗争的乐趣。
德金兄的另一部分诗作,则是“人在旅途”中极易产生的漂泊感,进而产生对于生命的无力感而发出的喟叹,他一定要将自己动荡的内心世界置入所到之处、所见所闻,与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虚无感作出斗争并最终作出妥协,“再痛,也要把血流向内心”(《老墨》)。而且比之前作品更加多变,更加立体,也更加熟练。
“在对视的瞬间
开始怀疑一本书的故事
怀疑这样一个平行的时空
阴差阳错的真实存在
渡己,却无法渡人
去到彼岸”
——(《彼岸》)
当我读罢德金兄2017年创作的新诗,对于他作为一个诗人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这些风格明朗、感情充沛、技巧完美的诗作,表达着他外化于生活的另一面,生命最纯粹的一面,代表着他个人的诗歌创作达到新的高峰点。
赵小波(诗人):
徐德金的年度诗歌,一改之前唯美、奔放的风格,以观察细腻,描述朴实,语言内敛,内容厚实的风格,体现着诗人的生活积累丰富,思考日益深刻,以及艺术风格的转型。年度诗选的作品,绝大部分近似于白描式的诗句,表现出对历史、社会、生命的热切关注。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精神史,文字记载了人类精神活动的艰辛经历。诗人与记者都担承着记录历史的责任。所不同的是,记者客观记录现实生活,而诗人俯视历史、现实与未来,以艺术的眼光,关照当下,思考历史,预言未来。徐德金曾疏离诗歌多年,他的近期作品,题材和风格的华丽转型,可能是他数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对现实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而后作厚积薄发的艺术展示。这是记者华丽的转身,也是诗人荣归的幸运。
朱必圣(诗人、评论家):
从德金兄今年(2017年)创作的这二十余首诗作来看,我惊异于他在表达上的创造性成就,简洁的形式传达出深刻的表达力;我还惊异于他的表达上的自由,有了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诗人拥有开阔的诗歌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