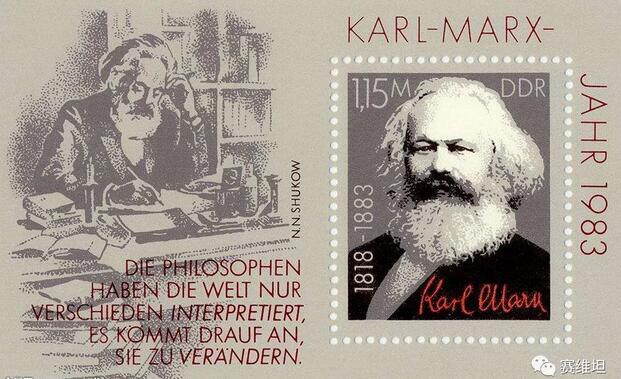
从某种程度上讲,科学对人的概念的影响,从神经认知科学打破灵魂的观念开始,将会随着人机结合对肉体的重新定义而结束。17世纪中叶,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宣称:人的大脑不同于动物的大脑主要在于皮质的量上,而人类比动物多出的大脑皮质即是灵魂的居所。通过人类认知科学的变革,人对自我意识的发现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在此之后,颅相学的进步发展,更使人摆脱了上帝的束缚,发现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说,“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而在此之后,这样的观念越来越得到深化和认可。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高呼“上帝死了”之前说道“我整个是肉体,此处无他”。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对人的意识进行了生物学的科学叙说,认为“习惯的形成可以被认为类似河流的形成……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有机物”,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论述。甚至于20世纪末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在《心智来自于物质》一书中,也引用19世纪中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一段话作为前言。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等,更是影响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一大批哲学家对人本身的理解。这一进程表明,科学逐步摧毁了人的旧有的灵魂意识,与之伴随的则是当代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
而这种自我主体的建立,将在新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展现新的变化。福柯在《自我的技术》中认为,自我关怀就是我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这种建构有两种方法,一是将一些人排斥在标识我们的范畴之外,即对“疯癫”的排斥;二是对所处时代最强有力道德系统的占有。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道德人格应当是那些学习如何理解自己的人。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可能会更加鼓励我们选择区别于此两者的第三种方式,即对自我的创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重估一切价值”,更是重估一切赖以重估的存在本身。人不仅要突破“话语关系”的束缚,还要突破肉体生命从而彻底地掌握自己。
这种进展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设想,因为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物质和社会环境的进步,最终的共产主义真正要实现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人的解放的基础,在于对人的本性的探寻。马克思所反对的阶级统治,实际上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业对黑格尔所谓的“人的本性”的掌控,也就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对“异化的东西”,即主体的掌控。在很大程度上,阶级统治同样也是福柯所反对的“生物权力”。福柯指出,在保障安定的秩序之下,人们“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也就是说,权力对人的生命进行调控,使得肉体本身成为权力规训的靶子。
那么,如何突破这种规训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呢?马克思指出,这需要从人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去寻求根本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解放,实际上就是劳动关系的解放,以及劳动关系之下的社会束缚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推动这种解放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重构世界秩序的主体力量。他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宣布迄今的世界秩序的解体,那么它只是讲出了它自己的存在秘密,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实际上的解体”。马克思由此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而在这一前景中,超越阶级的人的存在也具有了主体性和整体性。因此,马克思的解放思想有力促进了人类的自我认知超越个体性的局限和阶级性的窠臼。
但在福柯看来,马克思不过是以“异化劳动、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术语对世界进行了一种“简化神话”的自治重组,而并没有看到本质所在——政治的解放并非权力关系的解放。即使我们进驻于公社之中,我们仍在话语权力的束缚之下而难以自脱,权力无处不在。这种话语权力的真正解放会导致知识序列的崩溃,但同时也会导致人被彻底抹去。他讲到,人的形象的显露并非存在于客观性之中,而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一旦这种知识序列消失,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福柯看来,主体理论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此马克思不能够摆脱,他在主体理论之下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对政治束缚的解放,而非真正的对权力束缚的解放。然而,福柯在以自己的视角建立主体的同时,又摧毁了主体。他指出,灵魂不过是人们的建构,欲望也是如此,而当人们开始摒弃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了创造,由此就开始接近解放,接近自由。福柯的这种颇具现代性和解构性的观点,实际上也为人类的自我认识提供了进一步的视角和思路。
福柯强调“摒弃”,因为当人的知识层面的意义被抹去的时候,人就开始了认知自己的旅途。这样的观点也被近现代哲学家所推崇。例如,克尔凯郭尔就认为,人应当摆脱外在的一切束缚,才能获得自由,即“无限舍弃”。“亚伯拉罕的无限弃绝,意味着伦理有限性的终结,放弃外在的有限性,才能获得自身的直接性”。这也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标榜的“向死而生”。死亡是绝对的虚无,向死而生即是要突出死亡的核心地位,即“先行到死亡中去”,面对无限的虚无才能真正把握存在,获得本真的自由,“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种种潜在的束缚进行批判之后,认为社会应采取“总体性革命”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自由。“革命就是文化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和感性的、劳动过程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看到社会构造的自我背后隐藏的真正自我,才能够开始重塑自我的旅程。
思想家们对人的概念和人的自我主体性的思考,实际上为人类未来的发展与生存状况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人的基本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类能够在相当程度的生产力基础上真正成为自由人。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很可能让大多数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大量的闲暇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由人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则是人对于自我主体性的认识和反思,也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获得新的进展。尤其是在人机结合的预期之下,人类的生存状况将发生相当重大的改变,从而也会影响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但无论如何,这种发展前景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等人自由解放思想的要义的。只有当人类在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从而也才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人的基础。而在这一进程之中,人工智能无疑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自由解放思想的复兴有可能将重新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心灵的回归与自由在中国先秦思想家中多有论述,庄子是中国尤其强调心灵自由的思想家,更与前述许多西方哲学家有契合之处。庄子的先驱是杨朱,而杨朱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类似于柏林的“消极自由”的观点,即“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得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杨朱认为,人应该有拒斥社会控制的权利。如果社会或者国家以为天下做贡献的名义,而要求你拔一毛,那么之后就会以这个名义要求你拔更多,甚至于要求你牺牲生命。而基于重生的道理,杨朱不愿如此。
庄子则更进一步,“名者,实之宾也”。在庄子看来,那些苟利天下国家的话语,不过是权力对人的压迫的手段而已。若人沉溺于社会一切话语和关系中而不自知,就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好比“游于羿之彀中”。“异化”而不自知,终身难以解脱。而为了摆脱这种人生的“异化”,我们就必须回到自我的本真,个体的实现是一种“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过程”,进而回到“不思想的思想”,摆脱范畴的束缚,摆脱知识序列的束缚。而达到这种“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我境界,需要通过“以明、坐忘、心斋”等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强调心灵活动的至纯,唯有心灵的至纯,才能达到对现世的舍弃,进而达到对舍弃之后的创建和精神世界的扩张。自我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或言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这样的“天人合一”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是解放了的人。
(本文出自《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第269至第2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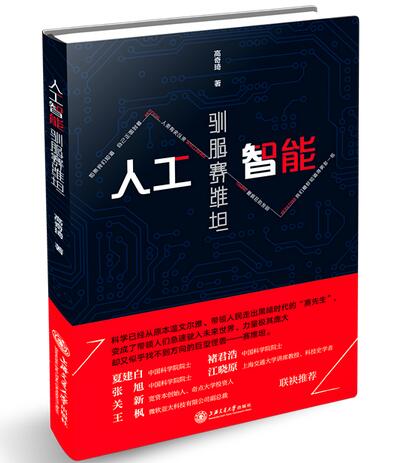
▍《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内容简介
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如同每一次飞跃性的技术革新都带来了整个社会层面的颠覆性变化,人工智能的诞生和进化,更可谓人类前所未有的疯狂发明。对此巨变,人文社会学界却少有足成体系的解析。而如若社会不能达成应有的平衡,科技进步带来的将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基于此,本书从产业格局、社会公正和人文伦理的层面,讨论了人工智能的未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及与社会之间喜忧参半的关系,并由之提出“趣缘合作”“数据生命体”“算法独裁”“透明人”等一系列科技与人文碰撞而生的概念。哪些职业将遭遇巨大冲击?现行的法律和规则将面临哪些挑战?人工智能的社会将给人性带来什么改变?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有待解答的问题。
▍《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作者简介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曾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奖励、上海市曙光学者等荣誉。以专家身份推动了全球治理指数(SPIGG)、国家治理指数(NGI)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数(CICSR)三大指数项目,并取得国内外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