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寓意本身与社会变迁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12月28日,长期关注这一研究的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张旭东在清华大学国情讲坛上发表演讲,他以“叙事与寓意:四十年按文学发展中的现实表现与形式创新”为题,以十年为一个阶段,考察每个阶段的代表性文学,试图说明文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价值系统等的互动关系。

电影《芙蓉镇》
1980年代新文学:看似断裂,实质是延续
张旭东认为,1980年代的新文学呈现的先锋和“断裂”背后实质仍然是对毛泽东时代传统的延续。他说,形式上的西化,否定工农兵文艺,想象力超前的现代派、先锋派文学的出现等,都让人们十分注重“断裂”的表层意义,感慨“觉今是而昨非”,1980年代的电影《噩梦醒来是早晨》可以准确地描绘当时的心态,人们感觉到的是“一切刚刚起步”,每个人都可以站在全新的时间节点上走向未来。
张旭东评价,这种“断裂”背后隐藏的讯息却是,越是否定,越是力图摆脱过去的阴影、越构成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某种“滞后”的表达。若深究文艺中的个性解放与文体创新,与传统进行决绝断裂的新式写作,深入考察这股文艺创新的社会力量,或可发现其根源或许来自于毛泽东时代“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社会逻辑;彻底否定旧秩序,创造新秩序,正是红卫兵的行动风格。因此,1980年代文艺创新与解放实际上带有早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痕迹。
此外,1980年代的新文艺也不断地追赶西方文艺,“希望做世界文艺的同代人”,为的是把中国文艺纳入到世界文艺,成为世界文艺的一部分,这种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希望,这种自我期待,在张旭东看来还不够深刻。因为这种追赶是对现代化思考方式有意无意的迎合,而文艺和经济或者技术不同,它并非从低级向高级线性发展。
必须指出,先锋派或个性派的这种追赶和创新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主流话语。回顾1980年代历史,不断冲破禁区的氛围也是全民共识,正是国家所期望的,所创造的,是各方面高度一致的改革共识,彼时先锋小说造反传统文学形式,模仿荒诞派,但却肯定现实,拥护改革,展现了1980年代生活新的可能性。
张旭东认为最有意思的文本并非现代派作品,而是那些既对知识分子暗送秋波,又取悦大众的作品,其中以电影《芙蓉镇》尤为突出,它由体制内电影厂出品,但它的批判性却远远大于先锋派文学。它不停留在反思“文革”,影片人物对“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诙谐解读(认为这侮辱性的对联既承认了夫妻名分,又支持了交配权利)直接解构了话语霸权,直击生活现实;最后,在影片主人公遭受不公待遇时,秦书田说的那句“像畜生那样活下去”,更是直接质疑了价值体系的荒谬,批判力度比现代派还要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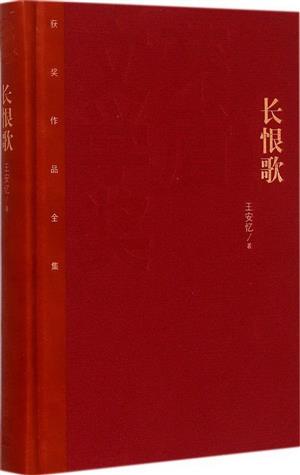
1990年代的文学:民众日常生活图景在文学世界的兴起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化开始,生活世界开始兴起,中国人开始拥有有私人生活图景,并且要求在文艺领域内找到自身肖像、兴趣、乃至共识。这最终使得描绘日常生活的文学和大众文化兴起,诸多影视作品如《活着》《编辑部的故事》《渴望》风靡一时。
除了影视作品外,传统艺术领域例如电影和文学,也出现了描绘民众日常生活图景的杰作。张旭东以田壮壮《蓝风筝》为例,电影从日常生活入手,描绘了一个儿童处理自己家庭的创伤记忆的故事。电影中铺陈了大量生活细节,准确细腻地传达出时代压抑的氛围。张旭东教授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电影的一大转变:回到小人物,开始讲故事,而这是1990年代电影很好的开局方式。
与《蓝风筝》不同,《长恨歌》则体现了上海怀旧的文化政治。1949年后,摩登时髦的上海在恢弘的时代中消逝。然而王安忆却着力描绘上海的小场景,例如流言,牌桌,马路,弄堂。这种民众生活场景在小说中仪式般地出现,为人们提供怀旧的对象。小说中的“上海小姐”们洗尽铅华,苟且偷生于上海弄堂;只要见到这些场景,我们就会想起,“我们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怀旧是对黯淡的当下的回应。

新世纪十年来最重要的四部长篇小说
第三个十年,也就是新世界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学出现了诸多长篇巨制,他们都试图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过去三四十年的历史。而文学写作的关注焦点,由宏大叙事转到“实践/行动中的中国人”。
张旭东教授认为,莫言在文学形式上把握了这个时代。其作品《生死疲劳》描绘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进入六道轮回后的生命体验,中国农村50年的经验浓缩存在于他的脑海中,而每一次轮回都带有生前的遗憾与切身痛苦,与化身动物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每次轮回,人的意识愈发薄弱,而这状态却让主人公“越来越进入自由的状态”,从而以简单动物的视角来把握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例如,在“猪”的生命形态中,适逢“文革”,他“过上了没心没肺般的开心生活”。“作为人,是糊涂的,作为猪,是清醒的”。而这个比喻正体现了莫言对时代的把握。
而在《兄弟》中,哥哥是纯粹无害的好人,英俊高大,没有性能力;弟弟则是他的相反面,擅长赚钱,性欲旺盛。最后,弟弟用钱把哥哥的骨灰送入外太空,“因为我们是兄弟”。余华通过对此“兄弟”的描写,展现善恶、道德、美丑,人与动物的对立统一,其中蕴含深沉的道德寓意:谁也看不上谁,离不开谁,谁也忘不了谁。
张旭东盛赞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了不起的小说,其语言和形式仿佛恢复了明清小说的生机与能量,这能量也来源于小说的描写对象,书中的河南人始终善辩,一定要把事情码得一清二楚方止。而在善辩的过程中,世相中的言辞、情理的多元交织维度得以展现。
而王安忆的《天香》描绘了明代江南,男性败家,女性不得不刺绣维持生活,最终代代传承。书中的劳动生产和合作一方面就是今天中国的隐喻,时至今日那种劳动图景仍然存在;王安忆更把自身写作劳动隐喻为刺绣,建立了自身与“行动中的中国人”的联结,并把这个联结放大到第三个十年的社会脉络中考察。
张旭东认为,以上四部作品旗鼓相当,为当代中国行动上的人提供了一种可供“摹仿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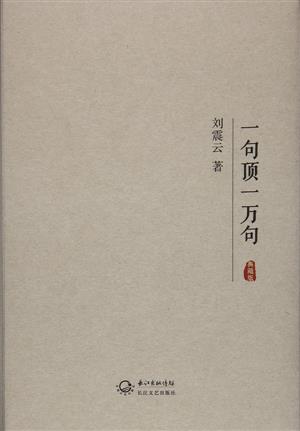
第四个十年及以后的文学将“内生性”发展
张旭东指出,从目前情况来看,第四个十年还未形成绝对性的风格,仍然只是前30年的延续。尽管文学历史研究者不应做无谓地假想,但仍可从社会现象中看出一些征兆,而这决定了未来文学的发展。
中国即将走入后工业化时代,而中等收入阶层基本上确立。这决定了再也不会有形式的断裂,思想观念的冲击也不会再如同1980年代那般给人深刻的震撼,文学的发展更需要内容、形式的内生性发展,并且持续加深。而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汉语的基本表意能力会不断复苏,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全面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而这是集体内在缓慢积累的过程。
回望过去近4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张旭东强调应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论意义出发,由生产方式和文化表象的关系来解读。即使是当下的历史阶段,我们仍然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逻辑来考察文学范畴内或委婉或扭曲的再现。尽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存在结构性的不相适应,但我们仍应在研究这近40年的文学时,看到文艺的半自律性,而非仅仅把文艺视为政治或经济、习俗的附庸或机械反映。文艺始终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地处于游戏状态与非功利状态中,为当下的我们提供自我理解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