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的同事马军兄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秘室编印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史学情况》(后改名《历史研究所简报》)中辑录出来的有关中外学术交流动态报道的汇编,时间从1979年至1983年,是一本反映中国国门重开初期中外学术交往状况的生动而且珍贵记录。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学术发展离不开交流,这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早在晚明,徐光启就曾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当然以交流为前提,没有交流哪来“会通”。自鸦片战争以降,中西两极相逢,中外隔绝之天下遂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在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学术当然也无法自外于世界,所以王国维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及其演进,无不得益于中外尤其是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是中西融汇的产物。那个时代辈出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就史学与国学而言,又以与海外汉学界的交流、对话最为密切。这种交流、对话与融汇甚至构成中国学术现代转向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对域外汉学的前沿动态及其进展格外关注,海外汉学史研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由这种关注产生的著译和评述文字之多可能超乎许多人的想象,马军兄倾十余年之力潜搜冥索,单相关文献目录就已累积了百数十万字,其中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已汇编成册先行出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桑兵教授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李孝迁教授编校的《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及《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等专书,即可略窥一二。当然,交流从来不会是单方面的,海外汉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种交流、对话,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汉学还是后来的外交官汉学,以及口岸汉学,那些在域外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多半不但具有各自的“中国岁月”,而且与中国学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如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理雅各、翟理斯,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福兰阁、傅吾康,以及美国的卫三畏、费正清等等,他们往来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为中国着迷”,才最终走上专业汉学之路。

费正清
然而,这种原本已越来越紧密的学术交流在1949年后却因全球冷战、意识形态至上而变得举步维艰,到1950年代末以后中西学术往来更几乎中断,中国学者出不去,外国学者当然也进不来。那个时候虽然也编译出版过一些域外汉学家的论著,如《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选译》《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外国对中国的研究》等,但基本上是作为“兴无灭资”的“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的,单从上述书名就可以嗅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火药味。这种人为的悬隔之局曾给中外学界带来了无限的怅惘。中国学人自然无从接触和了解海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域外学界,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也无法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亲自踏足中国,只能通过香港、台湾,甚至是日本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中国。譬如,美国知名汉学家魏斐德先生直到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好不容易才觅得一个机会,以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草药代表团的翻译和文化顾问的名义于1974年6月首次访华,得以乘机到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与蔡少卿、韩品峥、王庆成和陈大经等学者讨论太平天国史。十多年前,我专访孔飞力先生时,他也曾跟我提到他们那一代汉学家的无奈,他说:
对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来说,最不幸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1960、1970年代美国政府不让我们访问中国,中国也不接受美国人访问,两个国家分裂得很厉害,对立得很可怕。那时我很伤心,我研究一个国家却不能去这个国家,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放弃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准备转向学习和研究另外一个地方——日本。到了1974年,两国学术代表团终于可以互访,8月我陪同一个由十二位学者组成的植物研究代表团(The U.S. Plant Studies Delegation)访华,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先后访问北京、吉林、辽宁、陕西、江苏、上海和广东的植物学与农业研究有关学术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终于踏上中国,我当然非常兴奋。可是,那时正值“批林批孔”,气氛很紧张,每个图书馆都有高中学生把守,非常可怕。最可气的是没人敢跟我们说话,可能是他们担心被追究。这个我可以理解。不过那时我觉得有点伤心。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太平天国有兴趣,所以,我请求访问几位有名的中国前辈史学家,比如罗尔纲,但他们都说不方便。当然不方便,他们已经受过批判,不想再找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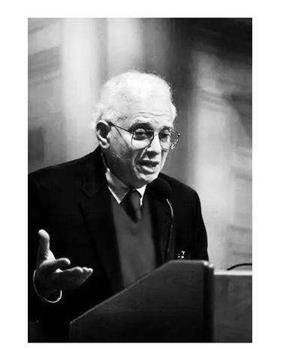
孔飞力
这种状况直到1970年代末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外学术交往才得以逐渐重回正轨。现在中外之间的学术交往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翻检马军兄选订的这本书,回到当初“重会”现场,中外学人那种如久旱之望云霓的急切,真有点恍如隔世之感。当年每有海外重要学者来沪演讲或座谈,上海相关学者往往闻风而动,倾巢而出。如1979年9月4日日本日中学术恳谈会社会科学者第一次访华团一行五人,在团长、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针生诚吉率领下访问上海,9月6日上午,访华团秘书长、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应邀在茂名宾馆作题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和日本的近现代化”的学术报告,到会者竟有7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图书馆、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除主持报告会的沈以行先生外,还包括顾廷龙、林举岱、郭圣铭、吴杰、陈旭麓、夏东元、梅公毅、汪熙、高文凡、夏笠、沈起炜、丁日初、刘振海、唐振常、方诗铭、汤志钧等知名学者。1982年6月2日,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刘广京应邀在锦江俱乐部作题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的学术报告,到会学者更多达二百余人,分别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等单位。这样的盛况,生动反映了上海史学界对海外新知新学的如饥似渴。同样的,对海外汉学家而言,终于可以到中国,与中国同行面对面交流,那种兴奋之情,很难用语言形容!1979年11月9日,法国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团到上海访问,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学者座谈,白吉尔夫人即难掩喜悦之情,侃侃而谈。且看当年记录:
白尔热夫人(现译为白吉尔夫人)以诗的语言,抒发她来到中国的无限喜悦的心情。她说她这次到上海感到幸福。十五年来她一直致力于现代上海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上海仿佛已成为她的第二故乡。接着她介绍法国汉学研究的概况。法国过去的汉学着重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物,而从事现代中国的研究,则是近二十年来的事。这是一门新开辟的学问。中国问题吸引了许多法国学生——多半是优秀的法国学生。在这领域里,法国和美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把汉学研究的力量集中在中国现代史。但是研究的重点又不相同。美国的汉学着重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法国的汉学,则侧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从时间看,美国汉学主要研究清末,而法国则着重研究民国。从组织看,美国汉学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大学和各中国研究中心,而法国汉学则集中于巴黎一地,分散在各机构,这些机构又互相配合。有汉学研究中心,即高等社会科学实验院,资料集中在那里,这些研究单位,多半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史,其重要专题为中国革命运动初期革命分子与国外的联系。他们保存着有关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巴黎勤工俭学的资料,其中1920—1924年资料齐全。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办了《少年》、《赤光》等刊物。其他专题为中国农村革命运动、人口与生产发展的关系、农民生活水平及其演变过程、农村土地制度与所有制的关系,以及农作物收成中地主剥削与国家粮食税所占比例等等。至于中国工人运动,谢诺(Jean Chesnaux)曾经进行研究,早已发表他的《1920—1927年中国工运史》,其续编《1927—1937年中国工运史》不久即将问世。
海外汉学家纷至沓来
正是怀抱这样急切而又喜悦的心情,一批又一批海外汉学家纷至沓来。仅就本书报道所及,短短不到四年时间里,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问,或历史所参与接待的海外汉学家代表团或个人即不下数十起。到访的代表团依次包括:美国明清史代表团(1979年6月23日到访,团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小韦克曼,副团长:匹茨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伊夫林・罗斯基,团员包括密执安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查尔斯・贺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菲利普・库恩、缅因州鲍登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约翰・小兰洛伊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韩书瑞、普灵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威拉德・裴德生、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斯特鲁维、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业键、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约翰・小威尔斯);日本日中学术恳谈会社会科学者第一次访华团(1979年9月4日到访,一行5人。团长: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针生诚吉,秘书长: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代表团(1979年10月13日到访,包括佐伯有一、卫藤沈吉、安藤阳子、安藤彦太郎等教授);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团(1979年11月9日到访,一行5人,包括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实验院历史学家菲雷先生、巴黎第三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白尔热夫人等);美国现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学者代表团(1980年1月12日到访,一行14人,包括保罗・柯恩、梅莉・戈德曼和詹森・派克等教授);日本日中关系史代表团(1980年9月10日到访,团长: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木村时夫,秘书长: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团员包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山根幸夫、东洋大学教授藤家礼之助、早稻田大学教授河原宏、早稻田大学教授大畑笃四郎、早稻田大学教授吉村怜等);美国历史代表团(1980年11月10日到访,团长:密执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维恺,副团长: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施金纳,成员有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学院讲师威廉・阿特韦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富美、耶鲁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员邓尔麟、宾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哈特韦尔、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希赖恩・麦克奈特);日本滔天会第二次友好访华团(1980年11月15日到访,团长:宫崎蕗苳,副团长:藤井升山、末松不三子,顾问:川田泰代、光冈玄,团员矢崎善美、江田等学者);日本“中国研究所”中国近代史学者访华团(1982年12月4日到访,团长:冈山大学副教授石田米子,秘书长:东洋文库研究员臼井佐知子,团员包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滨下武志、日中学院讲师佐藤公彦、东海大学讲师并木赖寿、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上田口信、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佐竹靖彦),等等。到访的个人则有: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秘书长、法国实验大学教务长施舟人教授(1979年11月8日),南斯拉夫历史学家阿里・哈德利教授(1979年12月4日),美国留学生韩起澜女士(1980年1月8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中国历史系陈学霖教授(1980年1月14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1980年4月12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博士(1980年6月11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继熙先生(1980年11月4日),西德历史学者蒂策博士(1980年12月4日),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中文历史系讲师多伍博士(1980年12月9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副教授横山宏章先生(1981年4月28日),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许进雄(1981年9月8日),美国俄亥俄国立大学教授朱昌崚博士(1981年12月24日),日本北海道大学副教授滨岛敦俊(1982年4月13日),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刘广京(1982年6月2日),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近藤邦康教授(1982年7月15日),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中国学及社会学教授、希伯莱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所所长史扶邻(1982年10月18日),美国访问学者柯临清(1983年1月26日),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佐竹靖彦副教授(1983年3月22日),美国缅因州科尔比学院艾尔曼教授(1983年3月11日),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历史教授徐中约(1983年6月),等等。他们在上海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一年半载,有的一两周,有的几天,但他们访问上海的目的不是观光,而是为学术交流而来。所以,一到上海,他们便迫不及待地与上海学者进行各种方式的交流,有的是座谈会,有的是演讲会,有的是拜会特定的学人,有的参观,有的搜集史料。对于他们的到来,上海学术界无论哪个单位负责接待,都会邀请上海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参加相关活动,相互交流各自的相关研究信息,但也有针对特定议题展开热烈、深入的讨论。譬如,1980年1月12日,应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美国现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学者代表团一行14人抵沪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14日上午,该代表团成员保罗・柯恩、梅莉・戈德曼和詹森・派克教授即与上海学者陈旭麓、汪熙、李龙牧、陈匡时、吴乾兑、任建树等举行座谈,双方就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问题进行率直坦诚的对话。关于这次座谈,本书辑录了登载于《史学情况》的相关报道,兹录其中“宾主重评洋务运动”一节,一窥当年中美学者对话情景:
在“四人邦(帮)”横行时候,为了配合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往往是同[卖]国投降主义联系起来,全盘否定。美国学者柯恩指出,“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你们对洋务派的研究也比较简单,没有看到其情况的复杂性,因而对洋务派、改良派作出区别,但我敢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是了解事物的复杂性,则两者越难区分”。陈旭麓教授回答说:区别还是可以掌握的,洋务派主要是引进西方技术,政治上则维护封建体制;改良派则不然,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故对洋务派人物,应该有一个具体分析,有爱国的,也有确是卖国的。即使是同一个人,也要历史地来看,具体地进行分析,可能这个事情上错了,而另一件事却是办得好的。以盛宣怀为例,有认为盛在政治上是不好的,他反对革命,但在经济上的一些活动还是颇为值得重视的。洋务派办的一些厂,没有办错,问题是在于没有办好。对李鸿章其人,现在也有了新的议论;对张之洞的评价,也比较高了,认为他的一些主张已远远超过了李鸿章和曾国藩。

汪熙同志指出:美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与我们不尽相同。他们往往把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混同起来,不加区别,认为中国的洋务派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事实上,象(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怎能列为改良派呢?这可能是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结构及其本质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他们对洋务派运动的研究,比较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的考虑即企业是属于谁的?在我们看来,洋务企业是早期官僚资本企业而非民族资本企业。美国同行还认为,洋务运动是从中国社会本身资本主义萌芽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比较强调内在因素,这点,我们觉得有启发,因为在我国学术界,比较强调外来因素,而对洋务运动如何从中国社会的封建体制下曲折发展等内在因素较忽视,这是个薄弱环节。
柯恩教授是美国麻省威斯里学院的历史系主任,是一位研究晚清时期历史的专家,他曾写《王韬和中国晚清时代的改革》一书,提出沿海和内地改良主义者所接受新思想程度不同的理论。这次,当汪熙同志问及他现在观点如何时,柯恩说,“现在我对自己在《王韬》一书中的理论也不完全同意了。中国的许多改良主义者,固然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更深,这是不能以地域来划分的”。陈旭麓等插话说:诚然如此,如康有为,他是沿海的,然传统对他的影响何等地深。反之,内地的谭嗣同,四川的宋育仁,则有新思想。可见,尽管在内地,通过某些渠道,同样传播了新的思潮。
涉及王韬,其社会影响不如谭嗣同,柯恩归因于内地人对于沿海学者的轻视。汪熙说不然,这是因为王韬的社会地位不如谭。陈旭麓则认为是因王韬思想的深刻性不如谭。
这里的柯恩,也就是柯文,他与陈旭麓、汪熙等先生在洋务派、改良派等问题上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但对话是坦诚的,也是富有卓识的。多年之后,我在专访柯文先生时,他还特别提及当年他与上海学者对话这段极其愉快的经历。王夫之说:“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这段话说的是心与物的关系,其实,学术对话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对话,中外学人各自“所存”才得以“显之”,出现“华奕照耀,动人无际”那样的智识景观。
俱往矣,这本书中记录的这段中外学界“重会”历史早已远去,为我们留下这一则则现场报道的学秘室各位老师也已一个个老去,当年亲力亲为审校这些报道的沈以行老所长则已去世多年,曾经刊载这些报道的《历史研究所简报》早已停刊,历史所也早已物是人非。但学术是靠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积累起来的,感谢当年学秘室各位老师的默默付出,为我们留下这份弥足珍贵的记录。当然,也要感谢马军兄一直以来致力于发潜德之幽光,把这份尘封已久的记录选订成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重温中外学界之间这段“重会”历史。
2019年2月18日

本文系作者为马军选订的《重会海外汉学界》一书所作序言,该书即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