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拿着奖学金去巴黎继续念书,还是该加入纽约著名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当吉丁再一次犯选择困难症时,他希望洛克——他最好的朋友——能给点明确的建议。但洛克只是冷酷地说道:“如果你想听取我的忠告,彼得,那你已经犯了个错误。询问我的建议和询问任何人的建议都是错误的。绝不要去问人家的看法。不要向他们询问你工作上的事。难道你还不清楚你想要什么吗?要是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呢?”洛克与吉丁从小一起长大,进同一所学校,念同一个专业,后来又做了相同的工作,但除此之外,两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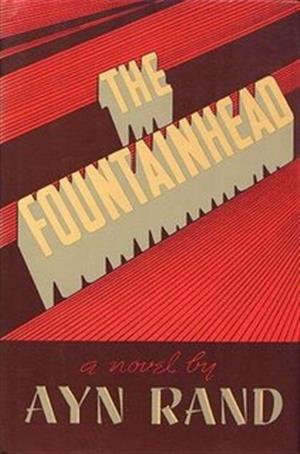
安·兰德《源泉》初版封面
《源泉》篇幅浩大,但结构清晰,作者安·兰德以平行对比的方式讲述了两位建筑设计师不同的职业生涯。虽然还有其余次要人物登场,但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而言,他们都只不过是主角的翻版,即心智上不是属于洛克人格,就是属于吉丁人格。这样的对立安排或许有点简单粗暴,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处在模糊的中间地带,但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简单粗暴是阅读乐趣的来源,因为很方便对号入座。逼迫读者在两种人格之间做判断甚至做选择,是兰德写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者而言,如果资本主义有什么值得捍卫的东西,那就是资本主义给予个人的自由选择权。

根据安·兰德《源泉》改编的电影剧照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
所谓的资本主义,指的是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中世纪封建系统瓦解后的产物,如今这种形态已蔓延至全世界。自十五世纪开始,西欧社会逐渐进入被后世思想家称作“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若把社会组织作为观测单位,可发现在资本主义时期,存在——或者说,形成了——大量被当下商学院教科书称为现代企业的实体。从行为上来看,这些实体以营利为目的,手上掌握着以土地、货币、技术、人力等要素为形式的资本,他们通过循环地将资本投入规模化生产以及商业交换等活动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虽然盈利性组织在中世纪就有,但由于当时受到交通、技术、人口等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规模只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所以这些组织无法通过频繁的再生产投资将自己发展壮大。相比而言,由于机械工业的发展和贸易市场的开拓,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企业有着大范围活动的能力,其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近可至邻城邻邦,远可至大洋彼岸。外加私有产权制度为个体追求利益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这种环境孕育出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在进步主义者眼里,这意味着两点:第一,“身体变得更自由了”,因为人不再需要像在中世纪那样依附于土地,只要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以养活自己,个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流动;第二,“心智变得更自由了”,因为资本主义能将足够多的人口纳入同一个空间,撑大的舞台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机会以及更丰富的想象力。
不过,自然主义者会反驳说,这种宏观意义上的自由增量并不能让人类摆脱生物学机制所施加于自身的限制性条件。人作为血肉之躯,该吃饭的时候得吃饭,该睡觉的时候还得睡觉。“更自由”并不意味着更好,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具体个人来说,其境遇既有可能变得更好,也有可能变得更糟,因为自由蕴含着风险。虽然所有人都想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但同时又害怕做选择,这并非因为当事人无法通过详尽的分析找出一种最佳选项去执行,而是因为当事人知道,所有后果都得自己承担。吉丁为了缓解心中的不确定感,向洛克询问意见,尽管他知道洛克不会给建议,因为他了解洛克的脾气,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去找答案。
在大学里听过名人讲座的人都或多或少见证过这样一番情景:在进入互动环节后,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生站起来,先自信满满地说上一大堆自己的看法,接着就怯懦地问演讲者“请问老师,能否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些建议”,讲座者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又要保持仪态,只能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一番。对于发问者来说,每一次询问都是一场转嫁责任的仪式——至少在心理上可以将自己的责任抛给建议者。仪式发生之后,倘若再遇到什么坏结果,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都是他们的错,谁让他们乱给建议”,接着就是门窗一关,两眼一闭,心安理得地躲进被窝。一次两次没问题,次数多了,人也就丧失了运用自由的能力。“自由的使用”是一门需要不断训练的技艺。吉丁的选择困难症并非一日养成,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就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们可以采取中性的立场,即:自由与桎梏是一对同时存在的范畴,不管人变得如何自由,桎梏总是如影随形,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就这点而言,资本主义在打断旧枷锁的同时也炼出了新枷锁。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枷锁,兰德说:那是他人的期望。
期望是什么?
吉丁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一种人生赢家的初始设想,家庭出生优渥,虽然父亲过早去世,但凭其留下来的遗产也过得顺风顺水,家里从小就非常懂事,会主动为母亲承担家庭责任,而且成绩好,相貌好,为人温文尔雅,有人缘,所以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认可声中,在临近毕业之际,同时拿到了欧洲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和建筑界大佬盖伊·弗兰肯旗下事务所的加盟邀请函。虽然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受到了学校与市场的认可,但建筑并非他愿意倾其一生的事业。吉丁一度想成为的是画家,只是在母亲不知不觉地推动下才走上了建筑这条路,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建筑是一种体面的职业”,而且,“将来在这个行业中遇到的人也都会是最优秀的”,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功。吉丁满足了他母亲的期望。
至于洛克,家境不佳,父亲去世之后,就一直自力更生,靠勤工俭学念完了中学,他在建筑行业里当劳工,“抹过泥墙,搞过测量,还炼过钢”,这些经历使他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大三结束时,因为拒绝修改自己不合格的课程作业而遭学校开除。他外表冷峻刚毅,对任何人都不会表现出情绪,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似乎满脸都写着“我不高兴”和“绝不妥协”。作为建筑设计师,他是乙方,出钱建楼的开发商是甲方。在很多人看来,乙方迁就甲方是天经地义之事,毕竟建筑师“是人,要生存”,何况资本主义的通行法则向来就是:资本的厚度决定话语权的归属。但洛克并不信这一套。当校长以过来人身份对他说“客户是将要住进你所建的房屋里去的人,你的一切得体的艺术都要符合他们的愿望”时,洛克却说“我无意于为了拥有客户而建造房屋。我是为了建造房屋而拥有客户”。
没有人对洛克抱有期望,洛克也不对任何人抱有期望,如果非要说有,他也只承认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他期望自己做出的每一座建筑都符合自己心中的标准。当甲方要他在设计稿中增加一些在他看来华而不实的要素时,他宁可去做绘图员、工地劳工,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因为他坚信“绝没有两种材料是类似的。在地球上也绝不会有哪两块建筑场地是完全相像的。绝没有两座相同用途的建筑。建筑的目的、场地和建筑材料决定了它的外形。如果没有一个思想主题,任何建筑都谈不上合理和美,而这个主题思想规定了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一座建筑都谈不上合理和美。一座建筑就像人一样,是具有生命力的。建筑的骨气就在于它恪守自己的精确度,遵循一个单一的主题,并且为自己单一的用途服务。”做建筑是这样,做人也这样,每一座建筑都为自己定义,每一个人也为自己定义。
所谓的期望,就是对一件事情或一件事物理应有的状态的设想,比如,“我期望我明年成绩更好点”就是说“我认为我明年的成绩理应更好”。但问题是,谁才有资格去定义这个“理应有”(ought to be)呢?在兰德看来,只有当自己面对自己时,才有资格下定义。可与此同时,兰德也警告我们:拒绝他人的期望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当吉丁已经取得建筑设计奖,在行业里如鱼得水的时候,洛克却连一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工作都搞不定,因为他的老板亨利·卡麦隆和他一样偏执,不愿牺牲自己的原则,结果就是找不到客户,接不了单子,直到公司最终倒闭。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成为洛克,还是愿意成为吉丁;第二,如果交朋友,你愿意交洛克这样的朋友还是愿意交吉丁这样的朋友。
洛克,还是吉丁?
在《源泉》所讲述的两段人生中,吉丁是起点高,终点低,而洛克则是起点低,终点高,无论是自己的理念还是产品,最终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还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事务所。读到这样的结尾,读者通常会长吁一口气,释怀地说:要坚持做洛克这样的人。在“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中,兰德写道:“《源泉》之所以具有如此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对青年志气的认可,同时它歌颂了人类的光荣,显示了人类的可能性有多大。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我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们要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
洛克象征新秩序,吉丁代表旧秩序,新秩序代替旧秩序是存在于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在这里,兰德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后果主义式的辩护,她试图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自我,就能赢来最终的胜利。但什么是“最终”呢?小说有最终,历史哪里来的最终?可能这次赢了下次又得输回去。作为读者,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若洛克的结局是不幸的,我们对他的态度会变吗?我们会不会称其为狂妄之徒?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讲,洛克这样的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少数,并不是愿意冒险的人少,而是选择冒险且又能活下来的人少,或者说,我们的眼界太有限。众所周知,百分之九十五的新创企业都活不过第三年,参与其中的创业者绝不乏洛克这样的人,但我们只看到那百分之五,并以为他们都是洛克,根据统计学的解释,这叫幸存者偏差。如果情况是这样,资本主义还值得辩护吗?
以对风险的态度来区分,洛克属于风险追逐型人格,吉丁则属于风险规避型人格。大多数人心里想着做洛克,但行动上,还是偏向于吉丁。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当面指出老师在处理某个问题时犯了一个错误,弄得老师很难堪,但同学们私底下却支持女生,说女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可既然是心声,为什么总指望着别人说?对于当事人来说,或许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有“心智与行为的偏离”,但如果摆脱先验式的价值预设,就能发现,两种做法其实都有各自原因,他们只代表了不一样的生存策略。两种对立的立场其实值得同等对待,因为人类的许多行为要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兰德推崇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因为雨果笔下的主角都带有个人主义英雄色彩,但她却没有注意到雨果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雨果眼里的社会复杂性。兰德的眼光是沙威式的二元对立。在《悲惨世界》里,沙威是苦役犯的儿子,他憎恨自己的出生,想使劲摆脱自己的出生,所以选择成为警察。他坚持法律、审查、权威永远是对的,相信犯过错的人永远不可能悔改,进过监狱的人即便出了监狱也只能是脱了囚衣的苦役犯。这种偏见使得他把追捕冉瓦让当作了终身事业。当然,雨果并没有控诉沙威,在小说中,冉瓦让也从来没有憎恨过沙威,因为雨果笔下的沙威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正直的人,若非真诚,最后也不会反思自己的信念继而投河自尽。对雨果来说,沙威的错并非来自人性上的恶,而是由于不幸经历造成的目光局限。
兰德相信,只有一种生存策略值得辩护,其余小人物都是可以抛弃的,而雨果却主张,对所有人都应该报以同样程度的理解,即便沙威式的人生也该得到尊重,我们应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雨果提出了一个兰德有意回避或无意思考的问题:世界上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生活在我们的眼界之外?
那些看不到的人
有一个人口总量为十亿的国家,其中有三千万人属于精英阶层,他们个个都是企业家,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拥有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其余九亿七千万人都是仅仅掌握生活资料的普通人,这些生活资料的获得均依赖于为企业家工作。假设突然有一天,三亿普通人被一票外星人一次性掳走,请问:那三千万精英阶层人士是不是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因为消失的不止有三亿人口,还有由三亿人口支撑起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当整个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同一时间内迅速萎缩后,一大拨企业就会因找不到产品销路以及上涨的人力成本而迅速破产,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企业领导者被迅速甩出精英阶层。
安·兰德的世界是由少数极为优秀的人领导和创造的,没有他们,世界毫无意义。但这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无意义的人,也参与了英雄的诞生,只不过是你没看到而已。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捍卫者,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供了与兰德不一样的辩护策略。对于前者而言,如果资本主义是好的,并不仅仅因为它能让优秀者脱颖而出(being outstanding)——毕竟对于好坏的评判取决于评判者的位置,更因为它所孕育出的包容性能让不同身份、不同才能、不同偏好的人自发地形成组织,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社会,成为有用的人(being useful)。
所谓的组织,是当人们为了实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目标时而形成的联合。对于原始人来说,形成组织的意义在于,共同抵抗大自然的风雨,赶走野兽,建起家园。人文教育的目标纵然是培养出拥有独立人格、有责任意识的人,但拥有独立人格、有责任意识不代表断绝与他人的联系。年轻人询问权威的意见其实没什么不妥也没什么可耻的,因为这是他们寻求联合的方式,从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理解这种行为只不过是承认个体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而已。因为不同的人出生于不一样的家庭,成长于不一样的环境,所以个体之间会呈现出显著的人格差异;因为他们会面临各种不一样且具体的问题,所以形成的组织才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诉求;正因为人是不完美的(imperfect),所以相互理解、合作、依靠才成为了必要的生存技能。
这关乎的不仅是诸如温饱、安全等人类最浅层次的需求,还关乎人类对于包括崇高、伟大、卓越等高层次追求。如果没有前赴后继的工匠,科隆大教堂不会像今天这样恢宏,因为这座大教堂建了将近六百年。仅凭一己之力,阿姆斯特朗也无法登上月球,因为背后是无数个工程师试图确保他的安全。同理,如果没有无数个吉丁这样的人存在,洛克也出现不了。当然,反过来想也一样,若没有那一个两个勇于挑战边界的人站出来,其余人也无法被组织起来。在足球比赛陷入低谷时,团队中需要有灵魂人物给大家互相鼓励,承托起团队其他人员的信任,否则只能一泻千里。我想,资本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尊重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如果你愿意和人联合,你总能找到合适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和别人联合,那你也可以找到一席之地。
回到前文留下的那个问题:你到底愿意和洛克交朋友,还是和吉丁交朋友?这取决于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既可以找个同类与你惺惺相惜,也可以找个异类与自己相互弥补,你甚至可以两类都找,只要你自身足够开放。好在,社会本身允许各种方案。
总结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的眼睛也总免不了偏见,无论是哪个伟大的作家还是不伟大的哲学家都一样。在这方面,安·兰德、弗里德曼甚至雨果都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拥有接近上帝的眼光。当我们只关注个人时,我们很容易忽视社会的力量,当我们只盯着社会时,又会限制自己对于个体的想象力。正因为此,所以除了眼睛以外,上帝还给了人类脑子,脑子的作用是“想”,帮助我们通过理性分析的能力来克服眼光带来的偏见。
有人会问: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会有偏见,那该怎么办呢?古希腊人提供了两种办法:第一,继续去看,通过不停的调整视角与位置去“看”,这叫外视训练;第二,继续去想,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训练自己的脑子,养成运用逻辑的能力去“想”,这叫内视训练。但无论哪种训练,若要有效,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承认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且自己愿意对这种复杂性保持持久的开放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