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宝玉、黛玉、宝钗到元春、袭人、刘姥姥,我们对《红楼》人物的看法充满了个人化的好恶,但只是印证既有成见的人物评论、褒贬之说本质上属于特定心理的宣泄。台湾大学教授欧丽娟的《红楼人物立体论》一书反对传统扁平式的《红楼》人物论,以“情节联系的有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双绾交涉的方法,发现“不疑处”中的矛盾奇异,以及“有疑处”中的人情事理,还原《红楼梦》人性世情中的复杂、深刻与丰满。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推究薛宝钗之相关论述之所以集中地向负面倾斜的现象,其关键因素正如夏志清所清楚指出的,乃是“由于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所谓“本能”与“感觉”都是受潜意识管辖的不自觉因素,建立在一种主观冲动的读者层次,而未上升至客观理解的研究层次。至于导致读者如此放任本能与感觉的偏爱,背后所潜藏之心理蕴涵,其一即夏志清所言,乃“由于读者一般都是同情失败者,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概将黛玉、晴雯的高尚与宝钗、袭人的所谓虚伪、圆滑、精于世故作为对照,尤其对黛玉充满赞美和同情。……(宝钗、袭人)她们真正的罪行还是因为夺走了黛玉的婚姻幸福以及生命。这种带有偏见的批评反映了中国人在对待《红楼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习惯做法。他们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并且是一部本应有一个大团圆结局的爱情小说。”这可谓切中肯綮之论。
但除此之外,人们之所以容易产生左钗右黛之偏向的原因,似乎还包括一种对“面具”恐惧、对小说人物寻求认同的特殊阅读心理需要。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脱离现实而个人主义浓厚的林黛玉相比,薛宝钗的存在样态与活动方式明显属于现实上“社会关系”的复杂再现。首先可以注意到,就如量身打造的蘅芜苑一样,曹雪芹不着痕迹地透过其建筑设计,微妙地隐示薛宝钗的性格养成与存在面相。第十七回中,小说的观照焦点随着游园诸人的脚步转向了蘅芜苑,并透过大家的眼光描述道:
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将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
事实上,被全部遮住的不仅是房舍主体,还更是屋主的内心世界,以反映出居所主人被礼教所围囿的处境,以及后天所培养的深沉隐蔽、皮里阳秋的性格。从而我们发现《红楼梦》中,作者自始至终即甚少着墨于宝钗的心理活动,读者对这个人物的认识,几乎只限于其外在举止而间接揣想得来。对读者而言,这位“藏愚守拙”的温婉女子一切表现皆动静合宜,在仪礼的规范中完美无瑕,却很难窥见人性中所本有的阴暗欠缺,与人心中翻腾起伏的喜怒哀乐,这些往往只能从她外在的言语行动中间接曲折地费劲揣摩,却又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就如其人所居的蘅芜苑一样。于是单纯者苦其绵密繁复,天真者恨其思深虑周,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潜意识便起而引发负面的质疑与丑诋。宝钗之所以常常被误解为城府深沉、富于心机,一部分的原因,恐怕也该归因于作者这样特殊的写作方式。
不过,薛宝钗之所以常被批评为虚假造作的原因,重点其实并不在其本心初衷的不纯真,而是指其言行作为所呈现的社会性。这是因为宝钗凡事不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不强调个人感受的重要性,也不以自我为终极考虑,因此不追求个人的价值实践。她总是将自我放在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人际网络的相对位置上来取得定位,相对于黛玉之以隶属个人范畴的“才情”与“爱情”为待人接物的出发点,宝钗毋宁是以群体生活中所着重的“伦理关系”与“世俗价值”为致力的目标。
所谓“伦理”也者,乃人与人在相对位置上交相互动所产生的关系,注重的是因应于各种角色扮演与身分功能而来的种种义务,而其表现必须放置于人际网络的“客观位置”以寻求合宜得体的范式,因此可以说是间接地建立在社会舆论的基础上。既然如此,一个处处配合伦理要求的人也就容易接受世俗价值的观念,因为“世俗”也者,即大多数人所遵行的生活总和,它是所有被括入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或最大交集面;以致接受世俗价值观的人同时也就容易取得社会群体的认可,而取得社会群体认可的人也不免进入到世俗的价值体系,彼此便形成了一种双向同构的循环性质。
这样一种富含浓厚之社会性的言行举止,为了要顺应外在之期许以避免与环境格格不入,必然是以抹除内在个性与自我感受为前提的。如同前述所言,在社会群体与伦理关系中,自我的呈现并不是从主观的“我”出发,而是将自我剥离出来,放在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人际网络的相对位置上,再透过他者的眼光来返照自己,由此而产生种种角色扮演与身分功能的认知。在这样一个由“他者”为参照点所建构的世界中,人的价值被强调的乃是“应然”而非“实然”,被赞许的是“义务”而非“权利”,被衡量的是“外在表现”而非“心灵感受”,被要求的则是“实践他者的期望”而非“满足自我的需要”,其结果便是个人的主观情绪被予以稀释或抹除。故余国藩亦指出:“自幼年起,宝钗就养成不受个人好恶左右的处世精神,也不会让自己的梦想与期盼有害他人。”因此,与其说宝钗为“假”,不如说其为“伪”;而所谓的“伪”,也应取先秦时的“人为”之意,如《荀子·性恶篇》所定义:“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宝钗的人格样态正是化性起伪、性伪合的产物。
相较之下,作为对照组的林黛玉,则有如玻璃打造的透明人一般,里外通透无碍地一览无遗,她内在的情绪变化、心思翻转和情感挣扎等等,一切都摊开在读者眼前而历历在目,使读者得以一步步探路取径,在登堂入室一窥其心府的悲苦凄愁、脆弱不安和孤傲自尊之余,便容易因了解而同情,又因同情而支持、乃至于认同,于是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观照立场和价值观的偏向。如果说,黛玉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用“探照解剖式”的,着力于层层挖掘透底,使人物里外敞亮明晰一览无遗,让读者可以得到完全的了解,因此是叙述观点与人物观点合一之后的产物;则宝钗乃是“投影扫描式”的,或云“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的叙事角度,其摹写仅止于外表的浮现,只见其言语行动而隐藏心理转折,致使读者不免陷入于认知模糊的状态,可以说是叙事观点与人物观点剥离为二的结果。这种人物塑造方法之不同,也直接导致了读者在喜好上的偏向:大部分的读者偏爱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林黛玉,却质疑、甚至反感于现实中较接近于一般人的薛宝钗,因而形成了“右黛左钗”的普遍现象。
探究其原因,乃如小说家弗斯特所指出的,“我们需要一种较不接近美学而较接近心理学的答案”。以不可能现身于真实社会的林黛玉之类的人物为例,弗斯特以设问自答的方式说明道:
她为何不能在这里?什么东西使她与我们格格不入?……她不能在这里,因为她属于一个内心生活清晰可见的世界,一个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我们的世界,一个叙述者与创造者合而为一的世界。……人类的交往,如果我们就它本身来观察,而不把它当作社会的附属品,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浅或泛泛之交;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对别人推心置腹;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说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小说里也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补偿。就此一意义而言,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它已超越了可见的事实。
很显然,由于“阅读”本身所具有的补偿功能,使读者总是倾向于在书中寻找认同(identity),于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在“叙述者与创造者合一的世界”中所呈现的心灵透明清晰的人物,补偿了现实人生中追求互相了解、抹除人际隔阂的挫败,也因此在美学上吊诡地获得了较大的接受度。于是,林黛玉之所以可爱可亲,除了她孤零的身世所引发的对弱者的同情之外,她那不可能属于我们现实世界的完全里外如一的坦露率直,也使得在人生中深为人际关系所苦的读者得到了心理的补偿。因为来自人和人之间“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所造成的苦恼和伤害,在面对小说中的林黛玉时便毫不存在了,对于她,我们没有因“不了解”所引发的种种障碍问题,因而我们可以彻底解除心防,与她合而为一地同喜同悲,即使不能认同,也总不失同情;至于那“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八回)的薛宝钗,却因为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忠实再现了现实人际关系里“守”与“藏”的本貌,以及由它所带来的混沌不明和距离感,使人无法透视了解、逼近深入,因而不自觉地引发读者的防卫心理,而无法真正与她同情共感,终究导致情感认同的背离。
由此可见,无论是偏爱或是质疑,造成这两种不同情绪的根源,其实并不只是来自她们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差异,如一般红学家所主张的“真/假”“自然/人为”“神性/俗性”或“原始/ 社会”的对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来自于两人在作者叙事上呈现方式的迥别,亦即经由“探照解剖式”的层层挖掘透底而内外清晰呈显的林黛玉,使读者在阅读心理上感到信任而心安,因此无论认同与否,都能够予以接纳乃至同情;而薛宝钗则仅止于“投影扫描式”的外表的浮现,令人不易捉摸底蕴,因而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所引起的,也就是不信任而有所保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自觉的防卫与猜忌。再加上薛宝钗相对而言是个现实世界的成功者,于是保持“同情弱者”之心态的读者就更容易弃她而去了。这或许是小说艺术上有关人物塑造策略方面更值得注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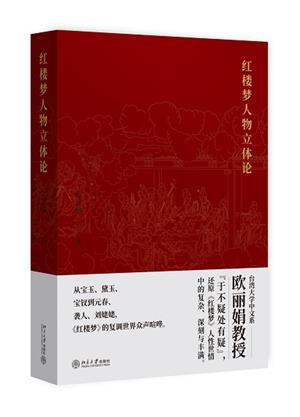
《红楼梦人物立体论》,欧丽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